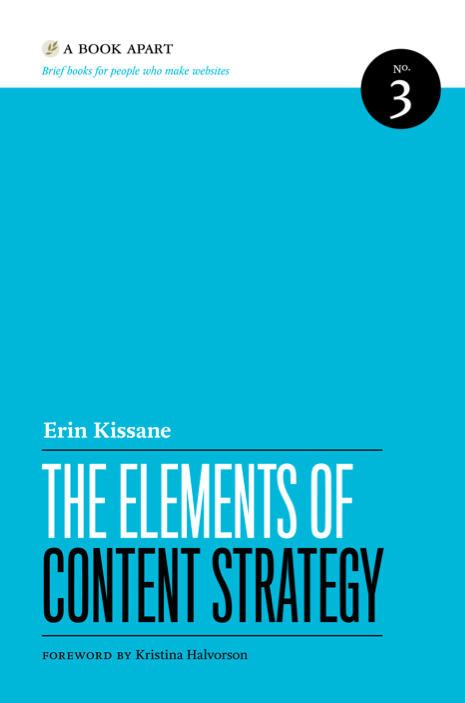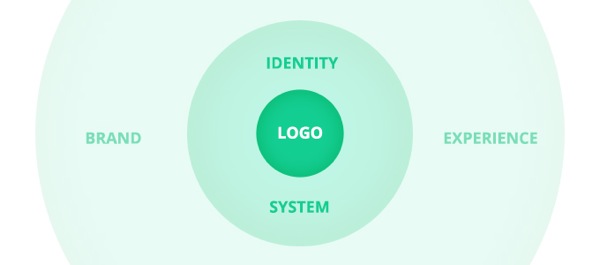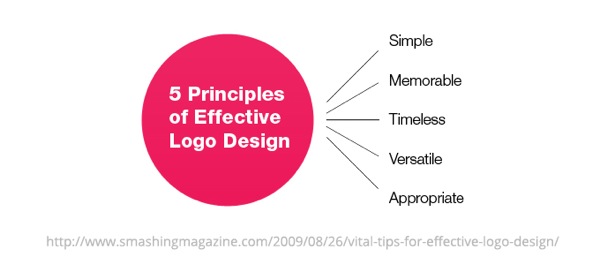本文由江南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张振东翻译,原文作者:Ian Bogost,原刊登于:The Atlantic,原文副标题:为何玩蠢蠢的游戏能缓解我们对现实的绝望。
http://www.bogost.com/writing/the_squalid_grace_of_flappy_bi.shtml
游戏,是个奇怪的玩意。
我不是在谈论《侠盗猎车手》或者《侠盗猎魔》这类道德低劣的游戏,在这些作品里,玩家需要去谋杀、打人和毁坏物品。我说的是广义的游戏,是指那些统称为“游戏”的形式。游戏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粗鲁而讨厌的痛苦,玩游戏,就像遭遇了一个卑鄙的流氓。你玩游戏的体验其实很像努力去让一个已经坏掉的机器重新运行。
在这个层面上,游戏和其他媒体是很不同的。确实,一部电影、一本书或者一幅画,能够描述卑鄙的感觉,也能让我们对不幸产生一种共鸣。但是和电影以及文学作品不同的是,游戏主要并不是去描述事件或者叙述故事。同时,游戏和我们说的体育运动也不一样,游戏不是为了展示我们强大的身体机能。和看电影、读小说或者欣赏画作比起来,我们感受游戏的方式是不同的。和跳舞、踢足球或者玩飞盘比起来,游戏的呈现方式也是不同的。
实际上,在玩游戏时,我们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。你可以说玩游戏和做运动有着类似的操作方式,你也可以说,游戏承担着类似于纯艺术和形体艺术的“含义”。但其实游戏里还有更多的玄机,游戏是让我们自己去操控设备。
有时候,游戏会让你模拟操控一个机械战士,或者去操控一个顶级运动员,或者操控一个星际战队,但更多的情况下,游戏是让你进行一些平凡的活动:比如《克朗代克接龙游戏》是让你把牌从一堆移到另一堆,《宝石迷阵》是让你调换临近宝石的位置,《吃豆人》是让你操控一个循环运动的、虚拟的大嘴。有些游戏的机制是非凡的,但大部分游戏的机制都是普通的,容易忘记的,低级的。
如果你回想一下昔日的经典《超级玛丽兄弟》,再想想超级碗星期天,你会发现还有许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经典游戏:比如象棋、围棋和双陆棋;再比如井字游戏、点格棋和填字游戏;以及比如大富翁、糖果乐园和飞行棋。这些游戏给人带来的挫败感强于带来的兴奋感,因为玩这些游戏尽管只需要很简单的付出,但它们总会伴随着相当大的痛苦。那还不是乏味或者愚蠢的痛苦,而是反复出现的痛苦;是那种你明明知道你要完成的目标,却总是达成不了的痛苦。那种痛苦也许是因为玩棋类游戏时孩子们那缓慢的游戏速度,或者因为玩民间经典游戏时别人深不可测的水平。相比较而言,足球通过展现人类身体和意志的努力,在各种情况下赢得胜利去展示足球之美,而飞行棋却因为刚开始做的一个决定,就可能让我们显得愚蠢和没完没了的痛苦。

继续阅读虐心的Flappy Bird